今年的寒假比较早,赶在了襄阳初雪前回来了,初雪一般都存不住,淅淅沥沥的。本篇文章实为个人感受,请不必评价,因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观众,冷暖也仅是自己知道。
另一件事就是回来送别“wéi爷”(土话,翻译过来是姥爷),去年送走了爷爷,我曾经说不希望自己回来面对的是一座座坟茔,所以在得知病重的消息后,确实放下一切赶回来了。此篇文章并不是卖惨或者品评什么,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回忆和无病呻吟的人,实话说这个小老头实在是不讨喜,也许有人会说死者为大, 不管怎样血脉确实是割舍不断的,确实可能会和怀念爷爷一样在某些时刻,他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。正如网上看到的,“亲人的离世,不是一场暴雨,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。”有些时候看到的只言片语,确实能泛起一片涟漪,经历过死别后,更是理解的如此深刻。
他其实有大半辈子时间其实在专营于让自己的姑娘照顾自己的儿子。或许是重男轻女的情节,又或许是“庄稼佬,维护小”。我妈经常会念叨他又要她怎样怎样,她奉献了很多很多给到了舅舅一家,给了娘家,但到底了还是在葬礼上望着姥爷那群酒友们,推杯换盏的时候对我说,如果你姥爷要不是得这个病,也许现在也和他们一样潇洒,喝着酒,吹吹牛。
葬礼很是风光,他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足够了解他爱面子的性格,按照农村的习俗,请了喇叭,摆了酒,买了实木的棺材,黑漆漆的,在大集(集市)十字路口表演了一个小时的拦棺,(农村的习俗,要求孝子、孝女,子侄们在出殡的时候跪在棺材前面,给烟,给钱点歌,以表现孝心和对亡者的不舍)十几个人一路喊着号子抬到了地里。也许是他确实不想走,不甘心,厉害的一路上掉了两次杠。
他的性格是真的很厉害,在家里说一不二了几十年,对婆婆(土话,指外婆)和他的几个子女呼来唤去了几十年,就连生命的最后还在呵斥,他的决定始终是不容置疑。出殡的前一晚要守夜,雨夹着雪,倾盆而下,漫天飞舞的灰烬好像是真的他在发脾气。
小时候的我并没有参加过这种葬礼,父母总觉得我是小孩子,去那些地方不好,小时候的确很害怕,对死亡。但是现在来看不得不思考以后,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形式的离别。回来之前,我是真的挺怕母亲伤心的,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在我眼里坚强的大人们,但是正如《请回答1988》中的德善看到的那样,母亲和婆婆他们和来参加葬礼的人寒暄,舅舅在一边磕头还礼,一切的一切就仿佛是一场平常的葬礼。大家上香、烧纸,吃席,谈论着家长里短,待到宾客走后,收拾遗物,上坟......母亲仍旧是那个母亲,只是偶尔会望着大门口出神。
今年也是我思考死亡和生命的意义最多的一年,越想反而发现他没那么恐怖了,正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,死亡和出生是一样的未知,或许是解脱,或许是重新开始。就像自己想抓住时间不留遗憾一样,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就是这么的渺小,与无能为力,与其去不断的懊恼这些,不如去坦然面对,我们没办法不留遗憾的过完这个人生,反而人生中大多都是无趣的机械重复,重复的遗憾,重复的错过,重复的懊悔,最终都是尘归尘、土归土,可能完美的结局是可以存在于某年某月某日的梦里,也可能是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蔚蓝的天空尽头。
网上说,一个人的第一次死亡是生理上的死亡,第二次社会性的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,即没有人在记得他。我并不在乎我能被记住多久,也许这个博客也可能是我的电子骨灰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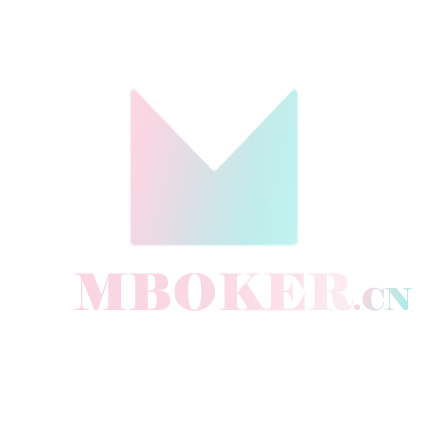 Terrence
Terrence  鄂公网安备 42060202000229号
鄂公网安备 42060202000229号
👍
💖
💯
💦
😄
🪙
👍
💖
💯
💦
😄
🪙
👍
💖
💯
💦
😄
🪙